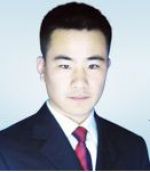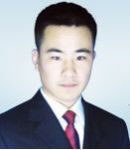律师随笔
从税制看改革开放(一)
作者:钟如超 律师 时间:2017年02月26日
本文多引用《对中国税制的看法》《中国税制》《中国税制论述》,具细无法提及,感谢上述作者对文章的贡献。
很多人对分税制陌生,其实,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分享分税制的红利:中央财政收入从分税制前的5千多亿元提升至目前的近2 万亿元,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以改观,进而使中央得以做许多多年想做而无法做的大事,如加强扶贫与社会保障,增加科教经费,实现军队不经商等等。
一、分税制前: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,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“弱中央”的状态。中央财力薄弱,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、国防、科教、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。
正是这场财政危机,让党中央、国务院痛下决心,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。
二、囊中羞涩的财政部长
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,就像家庭理财会议,讨论本年收入明年支出。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,财长王丙乾,中央财政十分困难,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,有一个大的窟窿,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,很多地方非常困难,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,中央没有钱给地方。王丙乾出于无奈,要各省作“贡献”,从1000万到1 亿元不等。
财政会变成了“募捐”会。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:“跟我要钱,我可没有!”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“反目”。“很多年过去了,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,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。”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。
“反目”有没有道理?有!比如广东,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“契约”,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.74 亿元,递增9%,再要钱就超出“合同”范围。但是,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,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,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,中央财政遇到困难,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。
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“借钱”的事,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。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,名为“借”,实为“取”,就是要地方“作贡献”。
财政会议还向地方“压”税收指标,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,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。因此,财政会议上“罗圈架”打得不可开交,税务局长跟财政部“打”,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“打”。税务局说:我们收不了这么多。财政部坚持不让步。当时,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,特别是富裕地区。
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,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,变成人们为“领任务”,分税“收指”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。
1992年,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。在工作交接时,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:老兄,我真佩服你呀,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?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。
刘仲藜感慨地回忆:“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。”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,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: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!
1992年,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,其中,中央收入1000亿元,地方收入2500亿元,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,赤字1000亿元,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。中央财政非常困难,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,朱镕基没有借答应。
三、中央财政难以为继
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,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:
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.2%,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;工商税收1400亿元,比上年同期增12% ,去掉出口退税10% ,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.4%.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.1% ,上半年达到14% ,比1992年GDP 增长12.8% 高出不少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,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,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。
税收增幅小,开支却大幅增长。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: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;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,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,如铁路、港口、民航等。按照往年的进度,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% ,而1993上半年为19.5% ,差了将近一半;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。
与此同时,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,一分也不能少。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,所以那一年,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,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,自然没借来。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。
今天我们回放此项改革的决策背景和过程,是因与10年前税制改革设计、实施的背景相比,今天我国深化改革与体制完善的国内外背景更加复杂,改革和发展的难度更大。当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大局,寻找深化改革的新的突破口,着手完善已初见轮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,汲取过去一些重大改革所取得的经验,是大有裨益的。
上述内容多引用《对中国税制的看法》《中国税制》《中国税制论述》
很多人对分税制陌生,其实,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分享分税制的红利:中央财政收入从分税制前的5千多亿元提升至目前的近2 万亿元,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以改观,进而使中央得以做许多多年想做而无法做的大事,如加强扶贫与社会保障,增加科教经费,实现军队不经商等等。
一、分税制前: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,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“弱中央”的状态。中央财力薄弱,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、国防、科教、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。
正是这场财政危机,让党中央、国务院痛下决心,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。
二、囊中羞涩的财政部长
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,就像家庭理财会议,讨论本年收入明年支出。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,财长王丙乾,中央财政十分困难,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,有一个大的窟窿,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,很多地方非常困难,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,中央没有钱给地方。王丙乾出于无奈,要各省作“贡献”,从1000万到1 亿元不等。
财政会变成了“募捐”会。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:“跟我要钱,我可没有!”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“反目”。“很多年过去了,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,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。”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。
“反目”有没有道理?有!比如广东,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“契约”,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.74 亿元,递增9%,再要钱就超出“合同”范围。但是,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,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,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,中央财政遇到困难,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。
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“借钱”的事,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。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,名为“借”,实为“取”,就是要地方“作贡献”。
财政会议还向地方“压”税收指标,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,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。因此,财政会议上“罗圈架”打得不可开交,税务局长跟财政部“打”,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“打”。税务局说:我们收不了这么多。财政部坚持不让步。当时,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,特别是富裕地区。
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,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,变成人们为“领任务”,分税“收指”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。
1992年,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。在工作交接时,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:老兄,我真佩服你呀,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?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。
刘仲藜感慨地回忆:“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。”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,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: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!
1992年,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,其中,中央收入1000亿元,地方收入2500亿元,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,赤字1000亿元,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。中央财政非常困难,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,朱镕基没有借答应。
三、中央财政难以为继
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,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:
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.2%,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;工商税收1400亿元,比上年同期增12% ,去掉出口退税10% ,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.4%.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.1% ,上半年达到14% ,比1992年GDP 增长12.8% 高出不少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,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,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。
税收增幅小,开支却大幅增长。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: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;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,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,如铁路、港口、民航等。按照往年的进度,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% ,而1993上半年为19.5% ,差了将近一半;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。
与此同时,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,一分也不能少。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,所以那一年,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,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,自然没借来。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。
今天我们回放此项改革的决策背景和过程,是因与10年前税制改革设计、实施的背景相比,今天我国深化改革与体制完善的国内外背景更加复杂,改革和发展的难度更大。当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大局,寻找深化改革的新的突破口,着手完善已初见轮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,汲取过去一些重大改革所取得的经验,是大有裨益的。
上述内容多引用《对中国税制的看法》《中国税制》《中国税制论述》